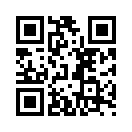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与河为伴,与水为舞,与死神赛跑,与人性的弱点斗智斗勇——
河神

水警在冰冻的河中打捞尸体
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水上支队的办公地点就在海河岸边,是一座普通的二层小楼,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天津之眼”。在风景如画的海河两岸,这栋小楼显得有些寒酸。

水警在河中巡逻
河神

水警在冰冻的河中打捞尸体
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水上支队的办公地点就在海河岸边,是一座普通的二层小楼,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天津之眼”。在风景如画的海河两岸,这栋小楼显得有些寒酸。
但走进小楼,见到被称为“水警”的董队、张队,见到民警老于、老刘,见到常姐、刘姐,听他们平静如水地回忆曾经历过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水上救助,深夜卧冰、打捞浮尸、抱起高度腐败的躯体……这一个个令人惊悚的词汇从他们口中讲出,竟然没有丝毫波澜,只是汇成一句话——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才知道,若干年来,这座不起眼的小楼里藏着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我才知道,每当110报警响起之后,从这座小楼中奔出的民警恨不得第一时间将落水者救上岸来;我才知道,水警们是那些在水中消逝的生命最后的尊严维护者;我才知道,在我们这个城市,是这15名平均年龄48岁的民警,用自己的双手一次次托举起百姓的信任和期待。

水警在河中巡逻
快一分钟,就能添一根救命稻草
因为缺乏禁止在城市河流中游泳、滑冰、钓鱼的法规,在海河里游泳、滑冰、钓鱼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有人在游船通行的河道上游泳,有人在冰窟窿旁边钓鱼,有人在薄薄的冰面上滑冰或者穿越。河流水深五六米,水下情况复杂,又多是淤泥和杂物水草。一旦落水,非常危险。但是,许多人明知此举危险,却总是侥幸地认为危险不会在自己的脚下,依然我行我素。
60多岁的张大爷,就住在海河附近。冬天到了,他和几位老朋友相约到海河砸坑钓鱼。他选择的钓点,就在距离支队办公楼约200米的河中央。他砸开个冰坑,优哉地坐在小马扎上,开始垂竿静候。老朋友们分别相隔几米,不时开个玩笑,对民警悬挂的“冰面危险不要踩踏”的醒目横幅视而不见。天气刚进二九,冰面冻得并不结实。民警杨学牧、常金良按照所里安排,一一劝阻钓鱼者撤离。张大爷脾气倔,一见杨学牧就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们警察快去抓坏人,别管我们钓鱼的事了。我就是掉下去,也有我儿子儿媳捞我,还轮不到你们管。”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民警谢长栓正在办公楼后的空地上整理出警装备,只听冰面上有人高呼“快救人啊”。他循声望去,只见冰面上人影晃动。一定有人掉进冰窟了!谢长栓一边喊队友帮忙,一边提起一块救援用的木板和救生圈直奔冰面。为了快速出警,民警们都穿着防滑鞋,谢长栓迅速赶到出事地点。此刻,冰窟里的人正双手扒着冰面,只有头部露在冰上。冰面不断塌陷着,水里的人一落一浮,眼看难以坚持。靠近冰窟,老谢伏身在木板上,将绳子一头拴着的救生圈抛到冰窟,气喘吁吁地说:“别怕,拽住绳子!”冰窟里的人最终在老谢和随后赶来的民警帮助下,安全返回岸边。上了岸,民警才发现,落水者正是张大爷。他一不小心,掉进了前两天别人砸开的冰窟。
张大爷在民警办公室换上了温暖干净的衣服。看到是警察救了自己,张大爷羞愧的脸“腾”地红了。
民警们说,在冰水里,身体再强壮的人,超过4分钟,也会失去力气,很快被冻僵丧失知觉。早一分钟救助,落水者就会多一分生还的机会。
河面微波荡漾,总会引发无限遐思,许多轻生者将河流选为人生的归宿。
初冬的一天,河风冷硬。一名中年妇女在河边徘徊许久后,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民警董清江、赵金伟接警后,火速开船靠近,但中年妇女拒绝救助,一次次试图远离救生船。水太凉了,中年妇女眼看着没了力气,下沉幅度越来越大。民警们果断抛下铁钩,准确勾在女人的羽绒服上,将她拉到船边,拽到船上。
救起生命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防止他们继续放弃生命之举。中年女人坐在支队会议室里,捧着一杯热水,等待家人前来。女民警尤晓静陪着她、劝她。看见一旁架子上摆放有斧子、凿子、镰刀、铁钩子,女人表现出疑惑的表情。尤晓静说,那些都是用来砸冰、打捞落水者的工具。女人歪着头想了想说,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在水里漂着,被钩子拽着。我不愿意这样死了,我也不愿意被你们勾来勾去。
尤晓静安心了。这些工具以别样的方式让轻生者重新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
水中的雕塑,就像一座丰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浮人,亦能俘人。
被救上岸的人是幸运的,但还有很多生命最终被河水吞噬。打捞浮尸,愈来愈成为水警的主要工作。每年,水警们要在河里打捞出100多具浮尸。
民警也有儿女情长,出警捞尸,对他们来说,每一次都是意志的考验,都是痛苦的洗礼。
民警们赶到发现浮尸水域时,周围早已挤满围观人群,像是在等待一场演出。多年的水上救险,民警们训练有素:打捞时不能有表情,因为说不好哪一个无意识的表情会被看客当做笑容拍下来发到网上断章取义地评论一番;不能喝水,因为有时候一次打捞耗时几个小时,水喝多了无处方便;不能发火,即便是在死者家属的谩骂声中,也要保持极度的冷静;甚至不能戴警帽,因为擦汗时可能会无意弄歪警帽,也会被说成有辱警容风纪……
一对外地的年轻夫妻带着父母到天津旅游。一家四口来到海河岸边的亲水平台。丈夫放下刚买的物品,对妻子说,我去河边洗洗手,然后径直走到河边。忽然,一瞬间,妻子只听见丈夫“啊”了一声,人已掉到河里,瞬间不见了踪影。家属们号啕大哭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报警。水警们乘船打捞,两个小时后,在200米外的河中央,才将小伙子的尸体打捞上来。躺在河岸上,那还显稚气的面孔谁看了都被揪得心疼。水警们将一块白布轻轻盖在小伙子脸上。这无人喝彩的打捞,总是在哭声中开始,又在哭声中结束。成功打捞,却不会有任何成就感。
面对尸体,他们也会恐惧,也会在内心有过片刻的犹豫;面对高度腐败、臭味扑鼻的残尸,他们从水中将肢体捞上来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餐桌上看到肉类,肠胃翻江倒海;面对家属悲痛欲绝的哭喊,他们的心里一样悲伤。
几位水警都记得10年前的那个元旦。那天中午,一名在卡口执勤的警察发现两名外地男子,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向外环线方向蹬行,形迹可疑。两名警察立即驾车追赶。两名男子分头逃跑。其中一人慌不择路,跑向一个结了冰的河面。民警紧紧跟上。他们在冰面上相距40米时,冰面突然断裂,两人同时掉进冰水……
水警们接到命令打捞民警遗体。他们远远看到,年轻民警的头颈部被冻结在冰面上,他的双手向上扬起,试图爬上冰面,又是一种拥抱的姿势。水警们含着眼泪,用工具砸碎围绕在民警身边的冰块,托住他、抱住他,生怕碰疼了他。
水警们讲述这个故事时,忆起当时场景,眼里含着泪水。我知道那位牺牲的民警叫杨燊,28岁,还没有结婚,照片上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我想,冰水中的杨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想到他的妈妈,一定想要去拥抱一个温暖的怀抱。
他如同一座永远的雕塑,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遗嘱,留在子夜的冰面上
“那一夜,我和董队趴在冰面上,黑暗中,我们相互留下了遗嘱。”副队长张吉静乐呵呵地回忆着他和队长董立军经历的两年前的那个深夜。
那是那年的腊月二十。中午,住在汉沽的居民老范兄弟俩和发小老李、老崔一起吃过午饭,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去蓟运河钓鱼。才到冰面上,老崔接到家里电话先行离开。其余三人说说笑笑地走到距离岸边约300米的地方砸坑垂钓。两个多小时后,老崔又回来找他们,只见河中央一个大冰窟窿,里面若隐若现能看见人的衣服……
三名群众落入冰窟!属地分局和消防部门紧急派员施救,但救援人员没有专用设备,无法靠近冰窟。水警们携带救援工具赶到现场时,天已全黑。三名落水群众的近百名亲朋聚在岸边,场面几近失控。因是暖冬,河面冰层平均厚度不足5厘米。
董立军和张吉静让其他人原地待命。他们趴在用以施救的木板上向事发冰窟爬动。漆黑的河面,不时传来的冰层炸裂声刺激着人的神经。冰水不时打到他们脸上,钻进他们的衣袖和裤脚,但他们竟然感觉不到冷,因为神经绷得太紧。
“吉静!”老董喊了一声。“董队,我在呢。”几米开外的张吉静答道。“吉静,一会儿到了冰窟附近,我先上。”“董队,我比你年轻,我有力气,我来!”“吉静,我是队长,听我的。我的捆绑技术比你好。只是如果冰面碎裂,我光荣了,还真有点不甘心啊!和弟兄们一起出警的工作还没干够呢。”听了这话,张吉静只觉得鼻子一酸:“董队,咱们救了那么多人,这水底不会留咱们的。”
200米距离,他们不知道爬了有多久,只觉得那么漫长。他们渐渐接近落水人员的冰窟,这时,更大的险情又出现了,越接近冰窟,冰层越薄。他们听到冰层开裂的声音,随时有落水危险。两人只能停下来,趴在冰水中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等待指令。
那是黑夜中的等待,两位民警趴在噼啪作响的冰面上,后面是300米远的河岸,前方十几米远处的冰窟,里面有生死未卜的三名落水人员。寒冷、恐怖、死亡的威胁笼罩着他们,而他们手边除去绳索和铁钩。黑暗的冰面上,两名人过中年的民警想到了死亡,而且相互留下了遗嘱。他们的遗嘱是什么,我不忍再问。那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更是人民警察不为人知的广阔胸襟。
按照现场指挥的命令,他们在凌晨爬回岸边。第二天清晨,舟桥部队援助的单人平底小船运抵现场。董队和张队再次返回到河中央,将三名落水人员的尸体捞起。
队有老于,爱好话剧
老于,名叫于之,59岁零10个月。
虽然年龄大,但出警时,老于常常跑在最前面。
那是2014年5月的一个清晨,天空晴朗。还不到6点钟,已经值班一天一夜的老于就把内务工作做好,将前一天出警情况写在记录本上,对出警后打捞出来的浮尸拍摄的数码照片也拷贝在电脑上,建文件夹存档。虽然退休的日子指日可待,但老于的工作没有一丝懈怠。
老于身高1.82米,乐观、开朗,在他几十年的公安生涯中,最初的10年和最后的10年,都和水上救援打交道。他不仅有着高超的泳技,胳膊上的肌肉尤其结实。老于说,这肌肉是这些年在水上救人、捞浮尸锻炼出来的,每次要将几公斤重的铁钩和绳子甩出去十几遍、几十遍,然后,再将沉重的浮尸拖出水面或者冰面,拖到岸上。没有把力气,干不了这活儿。
那天6点才过,老于和搭档就接到警情,晨练的人发现子牙河有一具浮尸。两人迅速出警。死者是个年轻女孩。老于心里一揪,可怜的孩子。老于将尸体抱上岸,交给属地派出所民警前,认真地为女孩儿整了整衣服、捋了捋头发。
刚要回队,又接到警情,相距10公里之外的一处水面也发现浮尸。老于和搭档赶紧往那里奔。
第二具浮尸还没有捞起来,第三起警情又到了,还是浮尸,还在10公里之外……直到那天中午,马不停蹄的老于还在忙,他和当天接班的同事一起打捞上来第五具尸体。捞这具尸体时,老于已经扔不动绳子,双手也不听使唤了。围观的人群起哄:警察下河去啊!警察去捞啊!疲惫的老于强压怒火,回过头说,别起哄,谁敢来帮忙?人群“呼”地退出去20米远,起哄的人一个也不敢上前。
老于说自己退休后会更忙,演话剧是他的爱好,他和他的业余话剧团演过很多经典剧目,他还演过《原野》中的主角仇虎呢。
也许,这支负责天津市区所有水域的生命救助、打捞浮尸及刑事案件中的物证、维护水上游船秩序的队伍,见惯了太多的人间悲喜,所以,他们才格外豁达、团结、珍惜生命、懂得感恩。流水不腐,逝者如斯,他们经历的所有惊心动魄早已随着海河平静东去,但是,河心的石头不会忘记,岸边的枝杈不会忘记,落水者的家属更不会忘记,是他们,被誉为“河神”的天津水警,用生命护卫着生命,用忠诚传递着真情,用奉献诠释着天津公安的英名。
责任编辑:新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