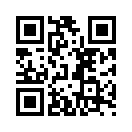小时候盼着过年吃麻花的情景,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关于煮麻花故事却是我永难忘怀的记忆


稷山麻花是老家晋南的传统风味小吃。亲朋好友来京,大包小箱总要带一些麻花来。因为是送给自己人,也想图一点便宜,他们大多是从市场上买散装麻花,包装也就谈不上讲究了。可近两年的景况不同了,不仅麻花的制作上乘,在包装上也不是先前的“下里巴人”了。更让我惊喜的是,在北京的一些超市,宾馆专卖店,稷山麻花也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麻花好吃,酥脆适口,油而不腻,地球人不见得都知道,家乡人却心知肚明。
可在物质匮乏、连肚皮都填不饱的年代,麻花可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的。那时,只有等到每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大人小孩才能品尝到麻花的美味。为了能吃到麻花,小时候和我一样的伙伴,都像盼星星般总盼着过年。甚至天真地想,要是天天都过年,那该多好啊!
在我的家乡一直沿袭着这样的习俗,一进入腊月,村里的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着煮麻花了。那时,家境都差不多,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全靠挣工分吃饭。你穷我穷,大家都穷。正因为如此,每逢年关将至,家家户户总是为煮麻花的事发愁。
有钱没钱,理发过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一家搭不起油锅,就几家联合起来,把瓶子里省吃俭用的油倒在一起,煮一点麻花过年。大人们的想法是,旧社会,杨白劳过年还要为喜儿买上二尺红头绳,一年到头了,再怎么着也得煮点麻花,让孩子们解解馋。
我记得很清楚,每年腊月天,家里煮麻花时,都是和本村的舅舅家搭伙一起煮。每当看到油锅烧热起泡,扑鼻的油香味从破旧的老屋飘向院落时,母亲和舅妈搓制的麻花生坯还没有下锅,我和弟妹们围着油锅,已经流出口水了。
尽管煮出来的麻花,有的长短不齐,粗细不匀,样子很难看,吃在嘴里却别有一番滋味。一般情况下,发酵好的面,搓完了,煮完了,还要切些馒头片,下到油锅里煮上一盆,毕竟烧一次油锅不是件容易的事。
麻花煮了一竹筐,我和弟妹们吃饱后,嬉笑而去。母亲还要把放在竹筐里的麻花,进行一一挑拣,分成几个档次,把炸得最好的留待正月天,招待亲戚用。
在农村,只有正月十五过了,才意味着真正把年过完了。这时,剩下的麻花,就成了稀罕物。为了防止孩子们偷吃,各家各户都要把剩下的麻花藏起来,所藏的地方,五花八门,各有千秋。我家也不例外。
那年的春节过后,母亲骗弟妹们:“麻花过年都吃完了,别像小老鼠一样还惦记着偷麻花吃。”原来,母亲不知啥时,早悄悄把积攒的一小竹篮麻花,挂到了家里高高的房梁上。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精心藏在房梁上的麻花,却被老鼠在夜深人静时从竹篮里偷出一条一条摆放在了落满灰尘房梁上。这是与母亲的一次闲聊时,二弟透露的往事。饭桌上,全家人笑成了一团。
如今,村里人的日子好过了,想吃麻花大多到市场上去买。而有的家过年时,还是宁愿辛苦麻烦,喜欢吃自己家里煮的大麻花。
岁月如梭,小时候盼着过年吃麻花的情景,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关于煮麻花故事却是我永难忘怀的记忆。
责任编辑:新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