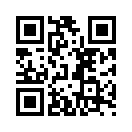一部新影片的上映,引发网友们和评论界的纷纷“吐槽”,俨然已经是当今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喧嚣热闹,众说纷纭,看客们得到身心愉悦,投资方当然冷暖自知。最近中招儿的,自然就是姜文的《一步之遥》了。也许,这部于导演来说是呕心沥血的作品,离经典真的只是“一步之遥”,却在人们的口水中落得黯然神伤。
批评者们最集中的意见,是说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了太强烈的自恋,并把这种自恋强行灌输给了观众。导演姜文当然很委屈,辩解说我一部电影拍了四年,我怎么还自恋呢?诚然,从筹备剧本到完工上映,秋冬春夏四载轮回,以导演为首的拍摄团队,自然没少下工夫。姜导的委屈可以理解,但他的辩词实在是笨拙了,有点急不择言的意思。明眼人都明白,四年磨一剧,却和自恋与否真的没有必然联系。
说起来,文化人似乎多少都会有些自恋。曾有个基层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北京找我,拿着一摞手稿,第一句话就说:我的作品,别人比不了。我一晚上就能写两段相声。他的话说的,本身就像相声,我不禁莞尔。但看他的作品,如预料中的平平。这说明,文人不论大小,自恋皆有之,且分不清程度的深浅。
自恋似乎也是有些益处的,不然不会如流行性感冒般流传。有句“心灵鸡汤”说:你若不欣赏自己,怎么能希望别人欣赏你。从励志角度讲,这话也有点道理。但这种自我欣赏是应该有度的,程度适合,可称自信;过度了,就是自恋。自信,人皆应有,否则难以成事。而自恋,我奉劝诸君还是清醒些的好,免得授人以柄。但话说回来,人一旦陷入自恋,劝他很难。
说到底还是个自律的问题。人若清醒,是看得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的,正确的态度就是欣赏和发扬自己的优点,抑制和摒弃自己的缺点。做人应如此,做艺术也应如此。说得直白,就是戒骄戒躁。骄傲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恶疾,成书于公元前的《圣经·箴言》,就有相当深刻的警句了:“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中国也有类似的古训,如“满招损,谦受益”,却可惜,能铭记在心的人很少。文化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也就自信有表达的能力,自信爆了棚,也就成了自恋,自己在自己眼里是光辉灿烂的,在别人却未必,这也就怪不得别人撇嘴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莫说自恋,自信也是要不得的。要夹着尾巴做人。但尾巴夹着并不舒服,所以在有些人眼里,文化人总爱翘尾巴,也就必须总要受批判。现在环境宽松了,文化人自恋或自信与否,基本靠自身的修为,因此,强调自律非常重要,把握自信与自恋的界线非常重要。
文化人其实还有一种心态比较普遍,只是大概没有人愿意承认,那就是自卑。自卑是个很有趣的东西,文化人的自卑往往和自信、自恋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呈此消彼长的状态。而自卑本身也特别复杂,往往并不局限于业务水平、工作能力的高低,而是涉及多方面。人可以因相貌丑陋自卑,也可以因身世贫寒自卑,甚至可以因为许多鸡毛蒜皮自卑。如想整容的小明星,并不难看的鼻子嫌矮了,整天耿耿于怀。文化人则有个好处,可以用自信甚至自恋与自卑抗衡。哼,你嫌老子长得丑,老子写得比你好。可世界是残酷的,尤其是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金钱俨然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写得好、画得好往往也没有用了,你可能换不来金钱。于是,自卑更甚,不平更甚,调节心态的自信崩溃,自恋也就扭曲。总说现代人是浮躁的,浮就浮在自卑、自信和自恋,如三只钓鱼的浮漂在心海的波澜里上上下下,甚至纠缠在一起解也解不开,别说钓到鱼,连平静的时候也没有了。
常在各种场合里看书法家写字,写的最多的,是“宁静致远”,也是一种自我鼓励或警醒吧。人要想做到“宁静致远”这四个字,还真的要好好修炼的。姜文导演的自恋,其实早在他拍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就有苗头了,不然何必非要在全国选一个和自己酷肖的男孩来演主角呢?片子成功了,提起此事也成了趣闻,甚至是艺术追求,但其中的其他,却被掩盖了。导演的自恋成就了后来的影帝夏雨,却似乎应该说毁了一个好导演。把“宁静致远”这四个字,送给观众期待的姜导吧。
责任编辑:新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