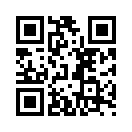昨晚去医院探望父亲,他似乎有点反常,特别唠叨。他穿着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倚靠在床头,橘黄的灯光下一脸的沧桑。只听父亲喃喃地说:“我不是‘二鬼子’,我是党组织派进鬼子据点的。”这是怎么回事?看我好奇,父亲便跟我回忆起了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
1941年,父亲13岁,割麦子的时节,大伯找到父亲说:“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父亲听后急切地问:“什么地方?”他神秘地说:“鬼子据点,给做饭的厨师打个下手。”“我不去!”父亲头一偏,一脸不愿意。大伯说:“你先去干着,到时保证送你去读书。”父亲这才勉强点头同意。
翌晨,有个姓范的师傅便带父亲来到山东泰安夏张地区鬼子据点。每天清晨,范师傅都要挑着两个木桶,将剩下来的饭菜挑去喂猪。他每次来都要关切地问父亲:“今天有多少日本人在据点里吃饭?”父亲便把每天吃饭的人数报给他。后来父亲才明白他是在摸敌情。这个据点驻扎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大约一百多号人,每天留在据点里有多少人吃饭,就能算出鬼子出动多少兵力。想到自己的工作也能抗日,父亲心里更有劲了。
一年多后的一天清晨,范师傅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带上自己的东西,今晚你就离开这里,送你去泰安军分区读书。”父亲听罢高兴得跳了起来,范师傅警惕地张望了一下,见四周没人,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父亲,神秘地说:“做晚饭时,记得将这包东西撒在大铁锅里。”父亲立马明白这是给鬼子下毒药。在据点的那些日子,父亲目睹了许多鬼子烧杀掠夺的暴行,早已恨得牙痒痒,爽快地接下了任务。
当天下午,父亲到厨房淘米,趁没人的时候,迅速将那包毒药撒进了大铁锅里,等米饭散发出喷喷香味后,便悄悄地回到宿舍,取了包袱直奔指定的接头地点。范师傅见父亲赶来后,急切地问:“那包东西撒到锅里了吗?”父亲点点头,他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让鬼子瞧瞧我们的厉害。”
当晚,泰安军分区的团委书记李发荣代表党组织送父亲去学校读书,李发荣对父亲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临上船时,他嘱咐父亲好好读书,并送了一支钢笔。
父亲后来听说,据点里的鬼子吃了下毒的饭后,七倒八歪地倒地呕吐不止,正巧有另一个中队的鬼子路过,发现据点里鬼子的惨状后,立即实施抢救,虽然救活了一些人,但大多已命归黄泉。这次中毒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日本鬼子,父亲至今也没搞清楚。而村里的人不知父亲是地下党组织派进去的,有人嘲笑他是“二鬼子”时,父亲也不敢解释,从不向外人说明其中缘由。
日本宣布投降后,父亲对这件事仍旧守口如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顾虑。父亲读书时,有个叫张建新的同学,因暑假期间到农村帮助农民搞减租减息,被日本鬼子抓去干体力活,曾帮助鬼子背过电台,虽然期间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最终趁鬼子不注意溜之大吉。但却因为这段说不清的事情,被大家认为是当过“二鬼子”,认为他有历史污点,始终没有被重用,只能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卫生所里干些杂活。“文革”中还被打成了叛徒,受尽折磨。
于是,父亲打鬼子的事就成了我家的一个不可触碰的话题,很少被提起。“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有一次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侮辱父亲为“汉奸”,父亲气不过动手打了他,父亲因此被当时炙手可热的造反派司令王洪文点名批判,结果再次被打倒。
1976年秋天,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终于熬出了头,被借调到市委工作组。父亲主动向组织提到这段压抑了几十年的历史,希望组织认真调查给予结论。组织上派人认真调查,最后给出了是党组织派进去,消灭鬼子有功的结论。
父亲离休后,每月工资1万多元,住院医药费全免,我有时开玩笑说父亲为党贡献不多,却享受待遇太好。现在看来,深入虎穴烧饭做菜,小小少年一下子消灭了那么多的鬼子,与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一样,也是英雄。
(作者单位:上海市公安局)
责任编辑:新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