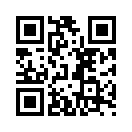春节之后,一位回乡博士关于故乡的描述搅动人心。说哀也罢,说怨也罢,字里行间,我读到的是浓浓的乡愁。
我以为,所谓乡愁,并非人人都有。一般而言,少年郎是没有的。他们正是在目光向前、喜滋滋飞奔快跑,冲向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哪里有什么闲工夫停下来,打量打量家乡的景致呢?更何谈为之生愁。久居乡里、未曾远行的人们大约也是没有的。他们听熟了乡音婉转,见惯了斯人斯事,心有所想,转眼就能听到看到,何来乡愁。
我还以为,所谓乡愁,可以无关年节,却会随光阴流逝、环境变迁而生发。词人蒋捷听雨,少年、壮年、暮年,歌楼、客舟、僧庐,年岁不同,处境不同,心情也大不同。羁旅之中,潇潇雨下,枯坐客舟,故乡与亲人遥不可及,眼前尽是“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天地间灰蒙蒙一片。即便是赳赳武夫吧,也难免怅惘。此时词人心中泛起的,倘若不是乡愁,还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乡愁从何时起开始在心底埋下种子,只知道,她确实就躲在某个难以察觉的地方,静待与你相遇。年龄越大,在外越久,堆积越深,相遇便会越突然、越频繁。
某一次我坐着公交车路过天安门,广场上游人如织,忽然不可遏制地想起家乡的某个雨夜。雨急风高,我们坐的公交车坏在了半路,奶奶挪着小脚,拖着幼小的我往姑姑家走。我头上顶着一方她的手帕。如今,奶奶去世多年,我们一起住过的老宅已空置许久。
大年初二,一场瑞雪飘落。我独自出了老宅,随意走走。街上人还不多,偶尔碰到三个两个,也都不认识了,不似当年的老街坊,彼此相熟。临街有几处老房子看上去颓废得很,几乎是随时要倒的样子。有一家的院门用砖头封了半截子,只有门框上红红的对联表明,此处还有人照应。路过广播局大院时,大门敞着,里边并无一人。那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不记得有多少个大年三十,我陪着他在里边值班。回家听哥哥说起,广播局已经搬走,那个办公楼马上也要拆除。
一切都在变。不巧的是,那些与故乡记忆紧紧关联的人与物,变得踪迹难觅;我们热切地希望着的故乡应有的模样,始终停留在想象之中。我们怀念而不见,渴望而不得,一切似乎未如我愿。我们也知道,这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仍会心有不甘,有些依依不舍,或者无可奈何,郁积久了,竟至成愁。正如暖冬的雪花融入大地一样,点滴点滴浸入心底。
(作者单位:公安部纪委监察局)
责任编辑:新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