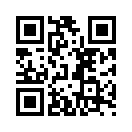当夜的凉风吹拂着大地时,我眼中的泪水一直未干。
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父亲去世了。当亲人真正离开自己时,我才发现自己欠父亲的太多太多。
小时候父亲教我写毛笔字的场景历历在目。父亲高小毕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也算是文化人了。过年时,附近三里五庄的村民都要请父亲写春联。每年从腊月开始,我家就在院子里摆上桌子为乡邻写春联。而当时年幼的我就成了父亲的书童,裁纸、拉纸、叠纸,怎么把纸裁得整齐,五言、七言、中堂怎么叠,福字怎么叠……父亲都一项一项教我。后来父亲开始教我握笔和写字,在父亲的熏陶下,我对传统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直延续至今。
农村的红白喜事,乡邻都是要随礼的。在这些红白喜事中间,有一个角色至关重要,那就是要有一个文化人把张三李四家随礼的数额账目一一登记下来,以便以后答谢人家。我的父亲常常担任这一角色。而我经常跟在他左右帮忙。最为得意的是在吃饭时,东家往往会单独准备一桌,端上四个菜,有时还和吹唢呐的、村上的头面人物一桌,很有面子。
从中学开始,我就一直在外寄宿读书。初中时每周回家一次,父亲总是骑着自行车将够我吃一两个月的小麦送往公社面粉厂,然后拿着面粉厂给的粮票,让我到学校换取食堂饭票。高中时学习任务加重,离家也远,基本上一学期回家两三次,父亲就借用村里的拖拉机一次性将够换我吃一个学期的粮票的小麦送到学校附近的面粉厂。1989年在我上高一时,母亲因病去世,从此父亲就开始了独居。随着年事已高,他开始在儿女家轮流居住。
父亲喜欢听戏唱戏。小时候只要有戏班子来,总是让父亲帮着张罗,每家每户收粮食,安排演员轮流住宿,甚至是白天搭台子晚上点煤气灯,父亲都是乐此不疲。渐渐地,父亲学会了拉弦子和唱样板戏。随儿女们进城后,他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常骑着自行车到小花园、白河边听戏、唱戏。
父亲为人节俭。儿女们给他买的衣服他都舍不得穿,总是藏起来,以致最后自己都忘了放在了哪里,身上总是那套十几年前的蓝色中山装呢子外套。给他的零花钱,他从来不用,就是在街上吃碗面条他也不舍得。
我到北京工作后,父亲在哥嫂的陪同下来过一次,那是2011年冬天,虽然下着雨,但我们还是陪他爬了一次长城。父亲回去后,常常在茶余饭后,向乡亲炫耀自己登上了长城,见过了“大世面”。
前年,父亲得了脑溢血。经过治疗才逐渐恢复,国庆节前,父亲总在打听我是否放假,并且每天坐着轮椅在院门口张望,哪也不去,饭也吃得很少。大家懂得父亲的意思,悄悄给我打了电话。我听后什么没说赶紧买了张机票往家赶。
我走到院门口,一股酸楚涌上心头,眼泪立马在眼眶里打转。年迈的父亲斜躺在轮椅上睡着了。我轻轻摇了摇父亲,他微微睁开眼,一见是我猛地睁大了眼睛,嘴角动了几下,眼泪便刷地流了下来。我想喊声“爸爸”,但是哽咽着却怎么也喊不出来。我紧紧抓住父亲粗糙发硬的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那么近那么真切。晚上,兄弟姊妹们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父亲坚持要坐在旁边听,一直到深夜。实际上他早困了,刚听几句便睡着了,一会醒过来继续听。半夜还支支吾吾说,等身体好一点了让我接他到北京住几天。
父亲再次摔倒了,这次是右脑出血。买不到机票,我带着家人转乘高铁往家奔。到家后已是晚上,父亲已经走了,临终前还让家人告诉我“估计北京去不成了”。
最后见到的父亲,安详地躺着,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村上乡邻都来为父亲送行,在这些身影中,有很多曾经见过的熟悉面孔,有的是在写春联时的现场,有的是在戏台旁,有的是在乡邻的红白喜事中。而这一次,是大家为父亲送行。
父亲走了,但父爱依然。
(作者单位:公安部宣传局)
责任编辑:新闻眼